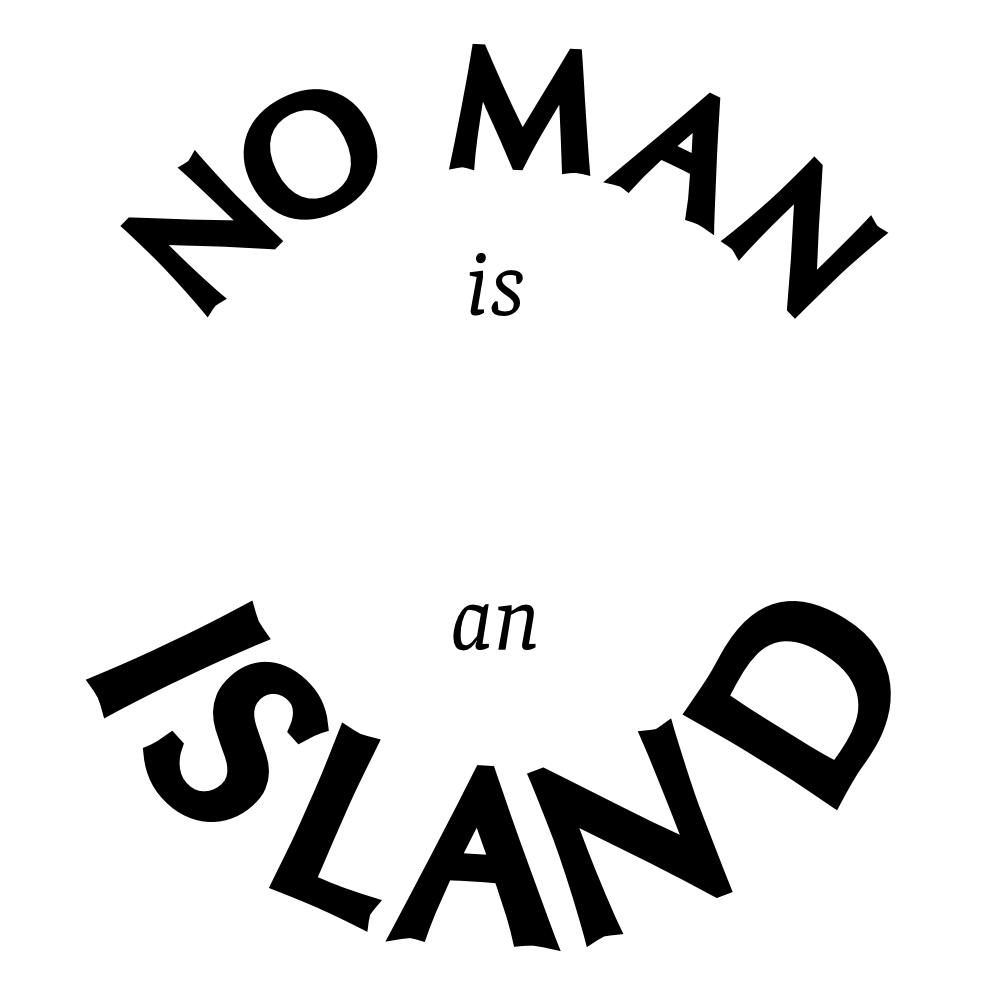丘琦欣
Languages:
中文 /// English
圖片:新能祭
丘琦欣採訪Sonia Calico與李彥儀關於3月19至20日在松山文創園區舉辦的新能祭。本採訪3月10日刊登在於Electric Soul,一本香港電子音樂雜誌。
丘琦欣: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
Sonia Calico:我是Sonia,我DJ跟artist name是Sonia Calico。我是一個做音樂的producer,我也是DJ,辦派對的promoter。這次要辦音樂祭。很難說我扮演的角色,因為都有一點。本來是比較想做音樂或表演的curator,但現在所有事情都混在一起。包括公關PR或行銷,還有一些舞台設計和各種體驗類的設計。我本以為音樂人辦音樂祭可以當吉祥物,但直接變成工友。
李彥儀:我是彥儀,我姓李。我一直都是獨立策展人,我自己原本對於所有當代藝術都蠻有興趣。因為因緣機會進到數位藝術節,後來成為著重研究數位藝術領域的策展人。
我自己喜歡的策展形式和我自己研究的主題跟失敗有關。我喜歡討論失敗或是被人家可否定的空間,開創一個我們都沒有想像的創意的領域。然後我覺得藝術家的作評,通常形容得很完美。但是我在研究失敗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創意的來源其實來自於很多錯誤所發展出來的想法。這是我策展的研究方向,然後我自己的策展的事件是用展覽作為我每一次對失敗這個概念不一樣延伸的研究。我是用展覽作為研究方法(exhibition as research)這種感覺。

Sonia Calico. 圖片:新能祭
我自己很喜歡策展過程會跟不同的觀眾互動。所以除了展覽的觀眾之外,也希望透過音樂方式reach到不同的觀眾。音樂也會呈現很多概念,甚至是音樂開創出的感受是很不一樣的。所以每一檔展覽,都會搭配派對或是一種聽音樂的活動。會配合展覽主題,然後找電子音樂人。找展覽的活動過程中類似的音樂計畫。後來因緣機會跟Sonia聊天。我們有很多共同朋友,後來聊到數位藝術跟電子音樂結合的可能性。慢慢從聊天聊到彼此想做什麼,她也在疫情期間看到了很多台灣的可能性,所有我們就開始計畫這個新能祭。
丘琦欣: 新能祭怎麼開始呢?
SC:很奇怪,怎麼在疫情中決定辦音樂祭?因為疫情時最不適合辦的時候。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我之前表演其實在國外比較多。在台北只會在一些地方表演,反正是朋友的活動。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就一直關在台灣。剛好我也出了我第一張專輯。專輯應該是一個很大的事情,但是因為疫情沒辦法tour。
當下也是很多國外的藝人也沒辦法到台灣,發現都排台灣的DJ。因為國外的藝人沒辦法進來,好像是一個好機會focus台灣自己本身的創作者身上。我除了辦派對意外還有一個音樂的廠牌,UnderU。和一個workshop叫做Beatmakers Taipei。這兩個地方,因為我這樣的廠牌所以。。。到底那個先呢?(笑)。因為這兩個project,我認識很多創作者。有很多創作者我猜想要做這個project?好像兩件事情是相輔相成的。但是我一直相信電子音樂真的要生根在台灣的話,一定要有台灣的創作者或是製作人。
因為這個文化是從國外來的,大家聽的音樂就是國外的音樂。我自己在創作的時候,也是聽他們音樂長大。但是我創作的時候,會把自己的想法放進去。也會把自己在台灣長大的想法放在我音樂裏面,我可以藉由這個跟台灣人溝通,其實電音不是表面上看起來好似是從國外來的東西,電音製作是台灣人做的東西把台灣人的想法放進去。這是我們溝通的渠道。
我之前也常提到搖滾音樂或是hip hop。這兩個音樂也是從西方來的。但是台灣已經有自己的模樣。台灣indie團,台灣indie的音樂祭已經怎麼多。可是二十年前不是這樣子,二十年前大家都是cover band都是唱Guns n’ Roses這類的。Hip hop也是,hip hop我們小時候,也有Luxy那時候,到處大家也都在放美國的hip hop。現在已經是大嘻哈時代已經可以當一個實境秀。他們在台灣都有自己的文化。我自己對電子音樂和派對的文化超級有熱情,我覺得這個東西很spiritual。雖然大家會覺得這很享樂主義,只是,但對我們來說不是這樣。感覺是我們的靈魂,一件核心。
因為在台灣很多比較大眾的想法覺得夜店文化只是信義區,撿屍,嗑藥。可是對我們來說不是這樣。裡面有很多很融合的東西。你會因為音樂而認識很多不一樣的文化。你了解怎麼叫做尊重跟你背景不一樣的人或是想法不一樣的人。很多是因為派對或是音樂我們才有這些想法。我自己也因為做電子音樂因此認識很多不同國家的人。以前,對台灣來說,台灣只是美國,英國,結束。可是我現在發行的廠牌雖然base在倫敦,他們大部分發行的東西是南亞的,不然是西非之類的。我跟他們合作的時候,我也更了解其他國家的事情然後真的直接認識他們的製作人跟他們溝通。這是一個很難得機會。
我覺得在台灣也可以的。不要只是外來的文化。最重要的是台灣有自己的創作者,更可以把這樣的文化帶進來。所以才會想用UnderU,發行台灣的藝術家跟製作人的歌。然後Beatmakers Taipei比較像workshop,這樣臥室製作人(bedroom producer)有個地方可以聊天,給自己一些友情跟信心,不然家裡作歌很容易自我懷疑就放棄不做。
我一直以來都在做這件事情,這個音樂祭對我來說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創作者,一路以來因為這兩個projects認識人。疫情當下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點什麼,讓大家focus在這些beatmakers身上,讓台灣人可以看到台灣人做的音樂很好,不需要只聽國外的電子音樂,EDM或什麼。
李彥儀:從數位藝術策展人的角度來說的話,之前譬如說像SOPHIE或是Arca,還有在日本可能跟我們比較近的Perfume,他們都會跟歌手或是電音製作人,然後跟視覺藝術家合作,做出很不一樣的MV或是演唱會視覺。所以我也在跟視覺藝術家合作過程中,特別在數位藝術領域,的確大部分在美術館展,但是美術館不是展示他最好的地方。因為一個是數位藝術的呈現方式大部分是在電腦螢幕上,或必須有不同硬體跟器材。
這些硬體跟器材都不見得是傳統一般當代美術館會有的硬體。再來,跟觀眾的互動性也是另外件事,然後整個數位藝術有沒有辦法在表演上面做更不一樣的呈現,這個也是在做策展中,每一次在策展的時候可以突破的一個目標。藉由這次新能祭可以跟電子音樂人合作。這樣在台灣也比較少看到的結合。其實這次我們邀請的藝術家們都本身很喜歡派對文化,他們都這塊很有興趣,但是沒有一個機會跟一個場合或舞台,促成這樣的合作。
丘琦欣:剛有提到戶外派對,因為在台灣很多辦的都在市郊,這次是在市中心。最近松菸也有很多活動。
李彥儀: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會想選比較在市中心的地方。我們自己也像選在市中心的地方因為我們喜歡城市的氛圍,希望可以跟其他音樂祭做出來比較不一樣的區別,交通比較便利,可能甚至從中南部來的人可以很快抵達到我們的派對地點。
SC: 因為我們也有數位藝術,也有真的實體的展覽品,在一個室內的地方是比較好控制。台灣音樂祭還是去山上或是海邊比較多。那樣要達成一個我們想的氛圍感受有一點難。
李彥儀:再來,是參加過一些國外的倉庫派對很喜歡這個氛圍,覺得倉庫派對整個空間,挑高的感覺,音響,是很其他場域很難比較有辦法取代的,然後是一個獨特氛圍。希望在台灣可以呈現這樣的感覺。
丘琦欣:台灣很少看到倉庫派對。
李彥儀:只要我們談這個音樂祭,很多人會提到南港瓶蓋工廠的派對。因為真的只出現一次的樣子。好像在他們心中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我們也希望新能祭也可以成為大家心中特別位置的音樂祭。
松菸真的規範滿多的。畢竟是一個古蹟,比較沒有辦法自由自在一點,是我們看過很多場地以後覺得最能呈現我們想要的倉庫派對然後挑高氛圍的場地,然後又是馬上可以使用,所以我們後來選擇這樣。我們這次選擇的一號倉庫,我們去到的時候,是真的覺得哇,馬上就有一個很不錯的感覺了。所以我相信到時候大家如果來,可能很少人可以看得到松菸這樣空曠的時候,應該會有驚艷的感覺,讓他們看到台北的場地又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圖片:新能祭
丘琦欣:這次怎麼選表演者呢?我看到的是滿廣泛的。
SC: 我覺得以DJ來說,我覺得以前在Korner的時候,大家都在那邊。後來,Korner關以後大家都好像你的人跟我的人這樣子。可是我反而會覺得辦這個音樂祭是我心中是讓台北的電音,這是我們的時刻。所以我會希望各種人都找一點,各種掛的。而且我覺得我們最少不要分掛,因為已經怎麼小的然後在分掛。其實大家都是朋友,只是大家其實說我們派對只會同掛的。可是其實大家都認識。
以前Korner大家不會說你是techno,你是house,或你是bass或什麼的。現在好像就很明顯。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定義我音樂的風格。我其實滿不喜歡這些貼標籤的行為。好聽的音樂就是好聽的,你其實要分就分不完。用什麼風格去把大家切開也沒意義的。
我們有找HH然後LUDU。我們很多視覺藝術家都是其實很多人有自己的音像(audio visual)表演的,他們很多是北藝大的。有很實驗很具藝術性的電子音樂,也有我這種。這些東西都是我喜歡的。平常台灣的活動不會把我們湊在一起的,那是我們的個性吧,因為我們不想分你是非主流,你是實驗。
李彥儀:有可能跟我們聆聽習慣也蠻像的,可能各種音樂都聽,然後各種藝術都會想要去了解。
我們也相信大概很多人跟我們一樣。因為我們身邊的朋友們,大家都是喜歡不只是一樣得東西,他們也很品味多樣,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會願意嘗試跟願意去了解。也許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那麼多采多姿的演出陣容的原因。數位藝術方面,我覺得我們都算是會看到一些藝術家的演出。都在我們朋友圈裡面,也都知道他們在做這種演出。他們通常有都在藝術的場域或是一些比較飾演的地方做演出。可能比較沒有機會接觸去派對玩的群眾。但也因為過去都這樣子,在不同場域演出,他們都有各自獨特的群眾。這次可以有一個地方讓他們都匯集在一起是我們希望達到的一個目標。然後希望大家保持的以嘎探索跟開放的心去接觸到不同的音樂。
丘琦欣:你會怎麼描述新能祭的核心價值或概念呢?
SC:去過很多派對。有一些派對的氛圍會讓你很舒服,有一些派對的氛圍會覺得好像要喝醉一點,不然喝太醉有一點危險。沒有玩得舒服的感覺。當我們要辦音樂祭的時候,我們也是想要創造出一個你要幹嘛都可以,但我們都彼此尊重。
李彥儀:我覺得跳舞是一個蠻療癒的事情。我之前住柏林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家門被小偷踢破了,我跟室友的電腦全部被搶走。後來就有一點覺得被針對,因為我們出門的時間非常短。沒過多久警察就打電話過來。結果,我跟我室友,我們兩個是女生,我自己就覺得怕怕的。那天就決定跑出去party,趴完就好了。
去派對的時候,就會感受到派對的人不是要佔你便宜或是也很希望你可以享受這個晚上。他們聽到很好聽的音樂就會跟你互動,但是他們跟你互動方式不是摸你或什麼,可能跟你微笑一下,或是問你還好不好。雖然是陌生人可是又是一種很親切的感覺。不是親密但是親切。這個感受會讓你覺得不只是家人跟朋友,而是陌生人可能也有可能會對你好。然後我覺得這會開創對話的空間或是跟不同族群對話空間的一個滿重要的奇蹟。之後你會對陌生人伸出援手或是提供友善的感覺,這種感受。
丘琦欣:所以對你來說派對文化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李彥儀:對,可能是沒有劃分那麼清楚的,就是一個家人與朋友之外的空間。當然也可以跟派對裡的人成為家人或朋友,但是就我自己經驗來說,我覺得跟完全不認識的人,你們馬上時因為在音樂的環境下可以有一種你知道他會尊重你的既有認知或共識。這很難得,我覺得在其他地方看不太到的。我曾經在台灣感受到這種情況一次,是在青島東路,就是學運的時候。有一點點有這種感覺。那個時候真的可以看到龐克的掛,嘻哈掛,然後獨立樂團,還有各式各樣的街頭藝術家在那邊塗鴉,然後穿上班族衣服也在青島東路上。你睡在那邊也不會怎麼樣的感覺。會有一種特別的安全感,社群的感覺很大,然後你們都有一種互相尊重然後聽彼此說話的想法。那個是我除了派對之外感覺的一次。

圖片:新能祭
丘琦欣:可以討論一下波疫情的派對概念嗎?
SC: 我們那個時候以為搞不好可能是解封後第一個音樂祭或是大的倉庫派對。後來就覺得還好,前面已經有一些。去年五月我們還不知道疫情會到什麼時候。 我們本來想辦十月,但是因為不確定移到三月。
李彥儀:前陣子Omicron在延燒的時候,很嚴重的時候,我們經歷一個很痛苦的時光。(笑)
SC: 覺得去年(2020年)五月又來了一次。
李彥儀:對呀,真的是惡夢。
SC: 關於後疫情的派對,跟音樂祭的主題也有關。因為有很多數位藝術跟電子音樂結合,大家創作很多次是圍繞著虛擬跟現實。我自己的音樂也是。很多我們數位藝術家他們想要討論的事情也是這樣,怎麼把現實做的最虛擬,或在虛擬世界著最現實的東西或什麼。大家都對這個主題很有興趣,就是說現在到底有沒有要分你身份identity是虛擬的還是你身份是現實的。還是這個東西對於現在的人來說,這兩個東西是一樣重要,一樣存在的。
我覺得再加上,疫情這個時候,大家都在家裡,參加很多虛擬派對。我們也有虛擬藝廊讓大家不用出門都有這些,後來才發現我們平常在做的事情不用出門也可以做。誰在跟我講這件事,我問一個藝術家疫情前跟疫情後有沒有什麼差別,他說沒有差別。反正他們都在家,在電腦前面。DJ可能出去表演的機會變少,但是後來發現,其實大家做音樂都在電腦前面。所以在電腦前面參加虛擬派對好像也是合理。
這個音樂祭也規劃很多線上活動,也有現下的活動發生這樣。所以我覺得用現在這個時間點講,其實應該是一開始因為那個時候有疫情的時候在想的。但是延續到現在是一個我們想要用這個大家在COVID封城的經驗然後去討論未來,不管是在藝術或在音樂然後派對這個方向前進的。
李彥儀:我們這次有辦虛擬藝廊。虛擬藝廊裡面有邀藝術家打造一個空間叫做House by Mozilla,然後去打造一個他們展示的空間。然後在裡面我們也要求了很多open call徵件的藝術品,open call徵件而來的藝術家,針對我們策展主題然後提出他們的作品,我們一起去選擇。
這次我覺得籌備虛擬藝廊過程中,覺得印象深刻且有最大區別的地方是,我們以虛擬世界探索為主,而不是複製實體空間到虛擬環境上。因為在疫情期間有很多這樣的展覽出現,特別很多原本說要辦然後後來沒有辦法辦的。大部分是從3D掃描或是拍很多照片,但是去到他們網站很像是在逛樣品屋的感覺。雖然這也是一個方式,但是我們跟藝術家們一直在想我們在虛擬世界參觀的環境會是怎麼樣的。我們可能很多實體上需要的程序與材料,可能現在都不用。然後我在電腦裏面看展覽的時候,打光跟實體的打光都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就改變了很多我們在想作品跟規劃作品的邏輯。
虛擬藝廊已經開幕,他從二月八號然後一直展到四月二十號,有三個藝術家特別為虛擬藝廊打造的空間,分別是 林子桓的《地平說》,吳維佳 veeeky《水皮》,XTRUX《虛擬曖昧》 。每一個空間都非常好玩。

圖片:新能祭
丘琦欣:那Sonia,你這次有什麼想法關於你表演嗎?
SC:一開始本來想說很忙所以不應該表演。真的很忙,但是還是決定要演。
我們這次也有一些策展規劃,把歌手跟製作人,然後數位藝術家,視覺藝術家湊在一起,弄一個audio visual的live。我這組我是製作人,我的歌手是阿爆,然後我們視覺藝術家是吳維佳veeeky。veeeky是我從以前一起辦派對的好朋友,以前還像是DJ duo。她幫我做過很多MV。
我很喜歡阿爆的音樂還有她整個人,她整個傳達出來的很正面的氣息。其實我覺得她做的事情跟我有一點像。阿爆也有一個工作坊,找原住民的歌手跟製作人然後教他們怎麼做音樂,幫他們發行。你聽她的音樂你就知道她一直都在傳遞這些東西,然後都是用一個很正面的能量。阿爆跟很多人合作,其實她自己專輯很讚,我覺得有她feature都會變成好聽。我就覺得她是一個很有音樂感的人。而且我那個時候問她不知道她聽什麼音樂,就是什麼都可以合的那麼好。像我們會做一些她唱一些古調到我做的beat裏面這樣子。這都是很令人興奮,我也很期待。我們昨天兩個人有練團,練完有更多想法,表演會很精彩。
丘琦欣:最後還有什麼想說對於讀者嗎?因為我們很多讀者在其他國家。
李彥儀:我們來了!下一站,東南亞跟香港!希望之後會往這個方向發展。我們也希望跟更多東南亞,菲律賓,等等。
SC: 我們第一年因為疫情想要把眼光放在在台灣的創作者,可是我們未來規劃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我們有五年的未來願景規劃。如果疫情OK,要邀請這些亞洲的藝術家一起來參與我們的演出。也可以讓他們,不管是藝術家或是製作人,來跟台灣的創作者合作,一起在新能祭表演一個特別的表演,特別的演出。
以後可以想像我們未來想要走向Sonar那種感覺,我們也想要有座談會,也想要有論壇。我們在這個音樂祭可以看表演,你可以party,我們也可以交換很多資訊,然後會發現新可能性,新能及的一個大家一起在一起有synergy的一個音樂祭。然後希望這個東西可以慢慢從台灣開始然後擴散到亞洲的其他的國家。